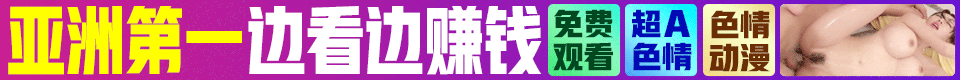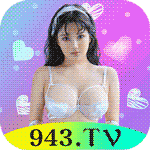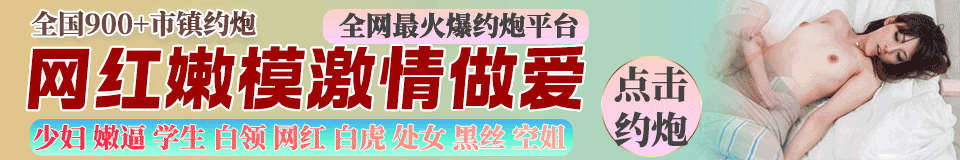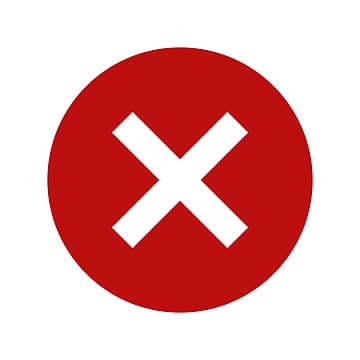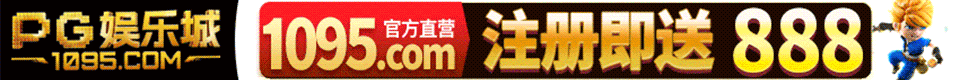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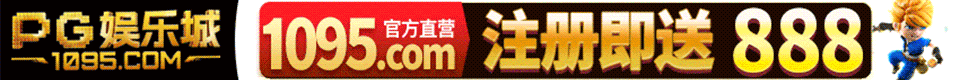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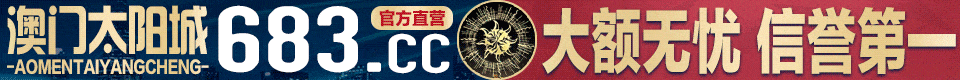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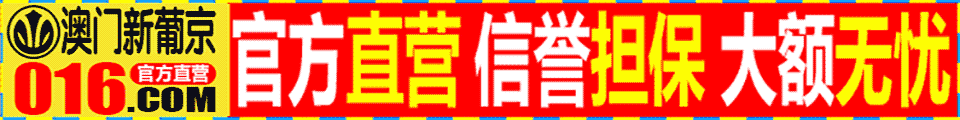














老公对不起 -是你的同事硬来的-我也不想这样子
大约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丈夫喝得烂醉如泥,丈夫的同事阿明扶着他回到我家,阿明趁我在厨房里的时候,突然抱拥着我,并将我占有了。
开始的时候,我是有激烈的抵抗的,但是阿明从后用手掌掩着我的口,他说如果我出声,就会弄醒我丈夫,到时就是有理也说不清的。接着,他一手将我的裙子揭起,还将我的内裤扯下来,用手指张开我的秘洞。
这样凶悍的淫乱动作开始时,我全身的血液也倒流,然而一种给火焰包著的热感,令我渐渐失去了自我,醒觉的时候,乳房已被阿明的两手抓着,完全露出的臀部给他拉近他的小腹,从背后插入他那粗野的男根。
阿明跨著伏下来的我,两手紧紧抓着我胸前的两团软肉,又浅又深地像是漫不经心似的抽插著,同时又拚命扼杀我叫出的呻吟声。阿明伸出右手向前,那张厚大的双掌摀住我的口,可是,如此给禁止发声,反而令我享受更深的悦乐。
阿明继续抽插,他的抽插把我直推高潮。
“哇!太太,妳连深处也在颤动了!”阿明下贱的说话,不断从背后传到我的耳朵里,同时把他的男根向我那柔软的深处强力地刺进去。淫秽的说话给我带来羞耻,但也令我更是兴奋,我的脑里,反复有“高潮”这个字句。
离厨房不远,在大厅的沙发上,我丈夫正睡得鼾声大作,这更令我觉得刺激万分,脑袋里变得一片空白。我二十几岁以来的人生,现在才接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高潮,我紧闭的眼睛,眼角渗出泪水,全身也痉挛起来了。
自从那一夜,我就像给阿明俘掳了一样,每当我丈夫往外公干,家里空着的时候,就会期待他和我电话联络,然后在酒店里和他热烈做爱,发出狂喜之声浪。面对着丈夫,我必须强制自己的言行,做一个循规蹈纪的女性,但是对着自己少一年的阿明,一切也收放自如了。
还有,全因为阿明每次拥抱我的时候也说惯了淫秽的说话,不知不觉之中我也习惯了,每次听到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便释放了我的淫荡性情,使自己也变得更兴奋了。但是,最是吸引我的,还是阿明那根长而粗的男根吧!实际上,阿明勃起的时候,足足比我丈夫大一倍,像棍棒一般坚硬的肉根,一经给它插进,就有一种充实感,我体内的肌肉,有若是熔掉一样,令我享受到炽热的愉悦。
三个月前,初次感受这种强烈的欢悦,就算心里是否定,肉体上还是记得清楚的。
下午,阿明离开公司,利用附近的酒店客房唤来了我。最初我也是犹豫的,但是一想到他那雄伟的男根,身体便告败北了。结果,我还是出发到酒店,烈日高挂的下午,我躺在阴凉的床上,有若一头白色的性兽,沉醉在男女交悦之欢娱里。
阿明想要怎样的行为,还有怎样使我难堪的体位,我也一一应允了,我浑身是汗地满足着他的种种要求,我背负著不贞的名字而浸淫于非常的淫乐里。
就算阿明想拍摄我的性器官的照片,我也欣然接受,干着那回事的时候,还允许了他录下音。女性最神秘的部份,给人拍照的羞耻,竟然唤醒了我自己本来也不知道的露体欲,和阿明一起听那些录音带时,那股烈火般的兴奋,又再探访我来了。
声带里的我,人格有若另一个人,下贱而露骨,好像自己是另一个人一样,令我更加兴奋。不过,应付阿明的好色要求同时,我仍是保持着应有的矜持。
这天的电话里,我知道自己竟然多了一个情敌,心里有如惨痛的刺伤,虽然曾经听闻阿明是有女朋友的,但是现在他却要我亲眼看他们二人的亲热,我的女性尊严绝对不能原谅,我对阿明的举动甚是愤怒。
但是,阿明绝情地对我说:“真遗憾,妳竟然不接受我和她的请求,我和妳的关系也好到此为止吧!”
这句有份量的宣言,令我慌张起来了,“等等啊,请告诉我酒店房间的编号吧!”狼狈的我,紧张的向着电话筒说出来。
“是嘛!我早知妳是明白道理的人啊!”在电话的那边,我感觉到他狰狞的笑态,我竟然不能下决心离开这样的男人,我亦有点憎恨自己。
“不过,我不要单是看的啊!在她之后,我也要你呵护啊!”说话的声线,连我自己也觉得是我是媚态毕露的。
“当然,和她干完后,我也会用妳最喜欢的大肉棍给妳满足啊!”阿明这样地说。我还听到一把年青的少女笑声,仿佛慢慢地走近他身旁。
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但是这样却令我心里烧热起来,大腿的内侧也变得湿润了。我步进寝室,取出新的内衣,我脱得一丝不挂,浑身赤裸。
和阿明相会时,往往也是替换了新内衣的。穿上新的内衣,便会浮现出那股气氛,更有充实感,更明白自己是个女性。
我穿着内衣之前,也会走到寝室里的镜子,看着自己的姿态。那美丽动人的青丝,披在标青的身材,配上俏美的容貌,自觉绝不逊色于那些模特儿或演员。竹笋型的一双乳房,配在纤细的腰肢上,看来便更见丰满;我一向自负自己是一个身材非常好的女人,我的大腿修长,腰的位置高,我就像一具白磁的陶器,雪白的裸体,非常均匀。
我穿上新的内衣,纯白的连衣裙上,再穿上一袭鲜黄色的外套。我关好了门窗,离开了豪华的住宅,登上了出租车。阿明所在的酒店,需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便抵达了。
夕阳照耀着我,我走进了酒店的旋转门,横过大堂,向升降机的方向步去。阿明在电话里所说的房间编号是二四二五室。登上了二十四楼,走进了静得可怜的走廊,按响了二四二五室的门铃。
门锁扭转,门向内拉进。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长发女郎伸出头来看,她鼻梁长长的,一张清秀的俏脸,她看到来者是我,便俏皮的笑了出来。
晶莹的眼睛、可爱的脸庞、明显是已赤裸的身躯,是用浴巾围着那赤裸的身体,想不到竟是她来迎接我。我因为对方的白晰肌肤,看得怔了一下。
“我是陈明丽,阿明在吗?”我勉强装得若无其事的说道。
“在的,请进来吧!”年青的少女笑着地领我踏进客房了。
“啊!妳真是很快哩!”双人床上,阿明早已赤裸的坐着,向我打着招呼。我将视线脱离他浓浓的腋毛,及那勃起如一柱擎天的肉棍。
“我要坐在哪里才好呢?”我将手袋抛在茶几上,拉长了嘴巴的说。
“这个嘛……就坐在对面那边的沙发吧!我要先请妳慢慢的欣赏。我先介绍方裕丽小姐给妳认识,她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她和我交往也有一年多了。她很可爱吧?连我的后门也很轻松地舔舐的哩!”
阿明吃吃笑笑的说著,那位年轻女郎也关好门回来了,他就面向她说:“向明丽打个招呼啊!”
“我叫方裕丽。”裕丽的面上露出喜悦的笑态,向坐在椅子上的我轻轻的低下头示意,然后就从抽屉取出一条尼龙绳。阿明也起身,下了床,从裕丽的手中接过绳子,慢慢走到我的面前。
“妳暂时忍耐一下。”阿明说著就用绳将我捆绑起来了。
“你……干……干什么?”
“没什么,我怕妳一时嫉妒心起,会在中途造成我和裕丽的麻烦,所以暂时要委屈妳一下了。”阿明将我的手反转到沙发的后面来绑起,摇动着股间那条红黑色的硬梆梆的肉茎走上了床。裕丽亦早已摘掉浴巾,赤条条地仰躺在床上等待着阿明。她的股间一片略黑的密草,盖在牛奶般美白的肌肤上,她肉体的每一寸都带有光泽,很是一种粗野而淫贱的感觉。
“舐啜我吧!”阿明向她施令了。裕丽给男性的肉棒接触著,便像一头白兔般的弯曲起来,她张开了嘴唇,将阿明的粗野龟头含进嘴里,一种淫贱的含啜声音,刺激了受绑着的我之听觉。
裕丽的长发披散,继续为阿明作口舌服务。一会儿,她媚笑着说道:“啊!我快要熔化了,上来给我插进去吧!”
阿明抬高腰在摇,我看在眼里,见到他抓着裕丽的玉手,像是女人忍耐不住似的样子,他的屁股上结实的肌肉也在抽搐著。裕丽像是取得胜利似的,骄傲地从嘴唇间释放了男性的硬直之物,双手将落在胸前的长发拨回背后,就坐上阿明的身躯,一对饱满的乳房就像跳弹著的摇动着。
“想进裕丽的身体吗?”跨著男人的身躯,她发出很骄傲的声音。
“是,想啊!快点坐下来啊!”阿明更用力地抬起腰部,像棍棒般竖立著的红黑色肉根,给那位年青少女的唾液弄得闪闪光辉。
“想进裕丽的这个肉洞吗?”
“想啊!快点给我刺进去吧!我很想快点捣进妳的仙洞哦!”
两人的淫贱交谈,配合著喘息不下的气息,在同达兴奋的情况下,裕丽将腰肢沉下去,一对男女交合在一起了。
阿明和裕丽,像是忘记了我的存在,她和他在一起呼叫、呻吟,双方也沉醉在肉体的交融里。不过,遭人忽视了的我,身体的深处也湿润起来了,若果两手是可以活动的话,一定会双手搔著这个闷痛的秘洞,现在,连我都极度兴奋了。
年青的裕丽,反心形的雪白臀部,像波浪般一起一伏,红色的湿润光泽,在那条秘缝露出来,阿明的肉柱,沾着她那种益力多颜色的女性液汁,反复地进出著。眼看着这个情景,加上湿润的液体撞击出奇妙的声音,令我更加兴奋起来。
床上的两人不断变换著姿势,男女的结合到了最高潮了,阿明的臀部肌肉剧烈地抽搐,裕丽也全身颤抖著,她的手指深深陷入男人的背肌,湿透的胴体紧紧缠着他的身躯,脚趾紧张地收缩在一起。我也是女人,当然知道裕丽这时正处于最兴奋、快乐的一刻,恨这时正让男人抽插的并不是我。
两人完毕后,也活像软泥般倒下,当肉体分开时,我见到裕丽的阴道口洋溢出阿明的精液,这种场面实在太令我羡慕了。这时我也奇怪,为什么我并没有妒嫉的心理?我觉得我的内裤已经湿透,好像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性交。
阿明慢慢地步离床边,他替我松绑了,并且扶我起来躺到床上,两人合力将我的衣服及内衣全部脱掉,一件不留。我像是受到催眠的人那样,失去了意志,让他们脱得一丝不挂,并给他们推到床的里面去。
阿明让我躺在他和林裕丽的中央,裕丽张开她的两腿,用纸巾揩抹著那些因为身体的活动而溢出来的液汁,接着也把我夹紧的大腿张开来。阿明指著还没有再勃起的肉根,要让我含着,我在沉迷中,使用口唇和舌头,将他的东西又含又啜,我不时也让口唇离开,发出“啊!呀!”的叹声,还摆动着腰部。
我给张开了的股间,正给裕丽舔舐著,像是石缝般的肉壁,每个起伏位也给她用舌头舐著了。这个裕丽,她还真有两下子,连我这女人也几乎被她溶化了。
我觉得我的肉洞竟然越来越湿润了!敏感的肉豆不断的跳弹著,我怎么也变成了这个淫荡的模样啊?裕丽的左手拨着我的薄毛,再啜下同性的朱色肉芽,裕丽的右手两根手指,就蠢蠢欲动的钻进我的秘洞。
“呀呀……不要!”我给反转身而伏著,面孔和头发也压在床上,阿明还用他的硬棍鞭打我的面颊。
“舒服吗?告诉我哪处最舒服啊!”
“那里……啊!下……下面的那里!啊呀!不行了!饶了我吧!”
激烈的快感,有如火柱般贯穿我的全身,下面的同性的手指不停在活动,我不期然的合得更紧,到最后决堤,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最需要的一刻,阿明才把他粗硬的大肉棒充实我,接着就是一阵子狂抽猛插,我高潮迭起,也不知流了多少淫水,直至他在我的阴道里射精,便倒下昏睡了。
其后又过了一星期,我丈夫回来了,但总是说话吞吞吐吐的,不过最后也说出来:“阿明那家伙,竟然盗取了公款,然后便人间蒸发;那个秘书方裕丽也不见了,看来她也是有份的。我们打开阿明的抽屉,发现了许多他和裕丽的做爱的照片,还有投稿到三级杂志哩!有些照片的女主角样子很像是妳,不过我知道不会是真的!”
我一口否定,随即便躲进厨房里去,两手掩著两行遏止不住的泪水,忍着哭声,不让我丈夫发觉。
大约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丈夫喝得烂醉如泥,丈夫的同事阿明扶着他回到我家,阿明趁我在厨房里的时候,突然抱拥着我,并将我占有了。
开始的时候,我是有激烈的抵抗的,但是阿明从后用手掌掩着我的口,他说如果我出声,就会弄醒我丈夫,到时就是有理也说不清的。接着,他一手将我的裙子揭起,还将我的内裤扯下来,用手指张开我的秘洞。
这样凶悍的淫乱动作开始时,我全身的血液也倒流,然而一种给火焰包著的热感,令我渐渐失去了自我,醒觉的时候,乳房已被阿明的两手抓着,完全露出的臀部给他拉近他的小腹,从背后插入他那粗野的男根。
阿明跨著伏下来的我,两手紧紧抓着我胸前的两团软肉,又浅又深地像是漫不经心似的抽插著,同时又拚命扼杀我叫出的呻吟声。阿明伸出右手向前,那张厚大的双掌摀住我的口,可是,如此给禁止发声,反而令我享受更深的悦乐。
阿明继续抽插,他的抽插把我直推高潮。
“哇!太太,妳连深处也在颤动了!”阿明下贱的说话,不断从背后传到我的耳朵里,同时把他的男根向我那柔软的深处强力地刺进去。淫秽的说话给我带来羞耻,但也令我更是兴奋,我的脑里,反复有“高潮”这个字句。
离厨房不远,在大厅的沙发上,我丈夫正睡得鼾声大作,这更令我觉得刺激万分,脑袋里变得一片空白。我二十几岁以来的人生,现在才接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高潮,我紧闭的眼睛,眼角渗出泪水,全身也痉挛起来了。
自从那一夜,我就像给阿明俘掳了一样,每当我丈夫往外公干,家里空着的时候,就会期待他和我电话联络,然后在酒店里和他热烈做爱,发出狂喜之声浪。面对着丈夫,我必须强制自己的言行,做一个循规蹈纪的女性,但是对着自己少一年的阿明,一切也收放自如了。
还有,全因为阿明每次拥抱我的时候也说惯了淫秽的说话,不知不觉之中我也习惯了,每次听到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便释放了我的淫荡性情,使自己也变得更兴奋了。但是,最是吸引我的,还是阿明那根长而粗的男根吧!实际上,阿明勃起的时候,足足比我丈夫大一倍,像棍棒一般坚硬的肉根,一经给它插进,就有一种充实感,我体内的肌肉,有若是熔掉一样,令我享受到炽热的愉悦。
三个月前,初次感受这种强烈的欢悦,就算心里是否定,肉体上还是记得清楚的。
下午,阿明离开公司,利用附近的酒店客房唤来了我。最初我也是犹豫的,但是一想到他那雄伟的男根,身体便告败北了。结果,我还是出发到酒店,烈日高挂的下午,我躺在阴凉的床上,有若一头白色的性兽,沉醉在男女交悦之欢娱里。
阿明想要怎样的行为,还有怎样使我难堪的体位,我也一一应允了,我浑身是汗地满足着他的种种要求,我背负著不贞的名字而浸淫于非常的淫乐里。
就算阿明想拍摄我的性器官的照片,我也欣然接受,干着那回事的时候,还允许了他录下音。女性最神秘的部份,给人拍照的羞耻,竟然唤醒了我自己本来也不知道的露体欲,和阿明一起听那些录音带时,那股烈火般的兴奋,又再探访我来了。
声带里的我,人格有若另一个人,下贱而露骨,好像自己是另一个人一样,令我更加兴奋。不过,应付阿明的好色要求同时,我仍是保持着应有的矜持。
这天的电话里,我知道自己竟然多了一个情敌,心里有如惨痛的刺伤,虽然曾经听闻阿明是有女朋友的,但是现在他却要我亲眼看他们二人的亲热,我的女性尊严绝对不能原谅,我对阿明的举动甚是愤怒。
但是,阿明绝情地对我说:“真遗憾,妳竟然不接受我和她的请求,我和妳的关系也好到此为止吧!”
这句有份量的宣言,令我慌张起来了,“等等啊,请告诉我酒店房间的编号吧!”狼狈的我,紧张的向着电话筒说出来。
“是嘛!我早知妳是明白道理的人啊!”在电话的那边,我感觉到他狰狞的笑态,我竟然不能下决心离开这样的男人,我亦有点憎恨自己。
“不过,我不要单是看的啊!在她之后,我也要你呵护啊!”说话的声线,连我自己也觉得是我是媚态毕露的。
“当然,和她干完后,我也会用妳最喜欢的大肉棍给妳满足啊!”阿明这样地说。我还听到一把年青的少女笑声,仿佛慢慢地走近他身旁。
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但是这样却令我心里烧热起来,大腿的内侧也变得湿润了。我步进寝室,取出新的内衣,我脱得一丝不挂,浑身赤裸。
和阿明相会时,往往也是替换了新内衣的。穿上新的内衣,便会浮现出那股气氛,更有充实感,更明白自己是个女性。
我穿着内衣之前,也会走到寝室里的镜子,看着自己的姿态。那美丽动人的青丝,披在标青的身材,配上俏美的容貌,自觉绝不逊色于那些模特儿或演员。竹笋型的一双乳房,配在纤细的腰肢上,看来便更见丰满;我一向自负自己是一个身材非常好的女人,我的大腿修长,腰的位置高,我就像一具白磁的陶器,雪白的裸体,非常均匀。
我穿上新的内衣,纯白的连衣裙上,再穿上一袭鲜黄色的外套。我关好了门窗,离开了豪华的住宅,登上了出租车。阿明所在的酒店,需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便抵达了。
夕阳照耀着我,我走进了酒店的旋转门,横过大堂,向升降机的方向步去。阿明在电话里所说的房间编号是二四二五室。登上了二十四楼,走进了静得可怜的走廊,按响了二四二五室的门铃。
门锁扭转,门向内拉进。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长发女郎伸出头来看,她鼻梁长长的,一张清秀的俏脸,她看到来者是我,便俏皮的笑了出来。
晶莹的眼睛、可爱的脸庞、明显是已赤裸的身躯,是用浴巾围着那赤裸的身体,想不到竟是她来迎接我。我因为对方的白晰肌肤,看得怔了一下。
“我是陈明丽,阿明在吗?”我勉强装得若无其事的说道。
“在的,请进来吧!”年青的少女笑着地领我踏进客房了。
“啊!妳真是很快哩!”双人床上,阿明早已赤裸的坐着,向我打着招呼。我将视线脱离他浓浓的腋毛,及那勃起如一柱擎天的肉棍。
“我要坐在哪里才好呢?”我将手袋抛在茶几上,拉长了嘴巴的说。
“这个嘛……就坐在对面那边的沙发吧!我要先请妳慢慢的欣赏。我先介绍方裕丽小姐给妳认识,她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她和我交往也有一年多了。她很可爱吧?连我的后门也很轻松地舔舐的哩!”
阿明吃吃笑笑的说著,那位年轻女郎也关好门回来了,他就面向她说:“向明丽打个招呼啊!”
“我叫方裕丽。”裕丽的面上露出喜悦的笑态,向坐在椅子上的我轻轻的低下头示意,然后就从抽屉取出一条尼龙绳。阿明也起身,下了床,从裕丽的手中接过绳子,慢慢走到我的面前。
“妳暂时忍耐一下。”阿明说著就用绳将我捆绑起来了。
“你……干……干什么?”
“没什么,我怕妳一时嫉妒心起,会在中途造成我和裕丽的麻烦,所以暂时要委屈妳一下了。”阿明将我的手反转到沙发的后面来绑起,摇动着股间那条红黑色的硬梆梆的肉茎走上了床。裕丽亦早已摘掉浴巾,赤条条地仰躺在床上等待着阿明。她的股间一片略黑的密草,盖在牛奶般美白的肌肤上,她肉体的每一寸都带有光泽,很是一种粗野而淫贱的感觉。
“舐啜我吧!”阿明向她施令了。裕丽给男性的肉棒接触著,便像一头白兔般的弯曲起来,她张开了嘴唇,将阿明的粗野龟头含进嘴里,一种淫贱的含啜声音,刺激了受绑着的我之听觉。
裕丽的长发披散,继续为阿明作口舌服务。一会儿,她媚笑着说道:“啊!我快要熔化了,上来给我插进去吧!”
阿明抬高腰在摇,我看在眼里,见到他抓着裕丽的玉手,像是女人忍耐不住似的样子,他的屁股上结实的肌肉也在抽搐著。裕丽像是取得胜利似的,骄傲地从嘴唇间释放了男性的硬直之物,双手将落在胸前的长发拨回背后,就坐上阿明的身躯,一对饱满的乳房就像跳弹著的摇动着。
“想进裕丽的身体吗?”跨著男人的身躯,她发出很骄傲的声音。
“是,想啊!快点坐下来啊!”阿明更用力地抬起腰部,像棍棒般竖立著的红黑色肉根,给那位年青少女的唾液弄得闪闪光辉。
“想进裕丽的这个肉洞吗?”
“想啊!快点给我刺进去吧!我很想快点捣进妳的仙洞哦!”
两人的淫贱交谈,配合著喘息不下的气息,在同达兴奋的情况下,裕丽将腰肢沉下去,一对男女交合在一起了。
阿明和裕丽,像是忘记了我的存在,她和他在一起呼叫、呻吟,双方也沉醉在肉体的交融里。不过,遭人忽视了的我,身体的深处也湿润起来了,若果两手是可以活动的话,一定会双手搔著这个闷痛的秘洞,现在,连我都极度兴奋了。
年青的裕丽,反心形的雪白臀部,像波浪般一起一伏,红色的湿润光泽,在那条秘缝露出来,阿明的肉柱,沾着她那种益力多颜色的女性液汁,反复地进出著。眼看着这个情景,加上湿润的液体撞击出奇妙的声音,令我更加兴奋起来。
床上的两人不断变换著姿势,男女的结合到了最高潮了,阿明的臀部肌肉剧烈地抽搐,裕丽也全身颤抖著,她的手指深深陷入男人的背肌,湿透的胴体紧紧缠着他的身躯,脚趾紧张地收缩在一起。我也是女人,当然知道裕丽这时正处于最兴奋、快乐的一刻,恨这时正让男人抽插的并不是我。
两人完毕后,也活像软泥般倒下,当肉体分开时,我见到裕丽的阴道口洋溢出阿明的精液,这种场面实在太令我羡慕了。这时我也奇怪,为什么我并没有妒嫉的心理?我觉得我的内裤已经湿透,好像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性交。
阿明慢慢地步离床边,他替我松绑了,并且扶我起来躺到床上,两人合力将我的衣服及内衣全部脱掉,一件不留。我像是受到催眠的人那样,失去了意志,让他们脱得一丝不挂,并给他们推到床的里面去。
阿明让我躺在他和林裕丽的中央,裕丽张开她的两腿,用纸巾揩抹著那些因为身体的活动而溢出来的液汁,接着也把我夹紧的大腿张开来。阿明指著还没有再勃起的肉根,要让我含着,我在沉迷中,使用口唇和舌头,将他的东西又含又啜,我不时也让口唇离开,发出“啊!呀!”的叹声,还摆动着腰部。
我给张开了的股间,正给裕丽舔舐著,像是石缝般的肉壁,每个起伏位也给她用舌头舐著了。这个裕丽,她还真有两下子,连我这女人也几乎被她溶化了。
我觉得我的肉洞竟然越来越湿润了!敏感的肉豆不断的跳弹著,我怎么也变成了这个淫荡的模样啊?裕丽的左手拨着我的薄毛,再啜下同性的朱色肉芽,裕丽的右手两根手指,就蠢蠢欲动的钻进我的秘洞。
“呀呀……不要!”我给反转身而伏著,面孔和头发也压在床上,阿明还用他的硬棍鞭打我的面颊。
“舒服吗?告诉我哪处最舒服啊!”
“那里……啊!下……下面的那里!啊呀!不行了!饶了我吧!”
激烈的快感,有如火柱般贯穿我的全身,下面的同性的手指不停在活动,我不期然的合得更紧,到最后决堤,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最需要的一刻,阿明才把他粗硬的大肉棒充实我,接着就是一阵子狂抽猛插,我高潮迭起,也不知流了多少淫水,直至他在我的阴道里射精,便倒下昏睡了。
其后又过了一星期,我丈夫回来了,但总是说话吞吞吐吐的,不过最后也说出来:“阿明那家伙,竟然盗取了公款,然后便人间蒸发;那个秘书方裕丽也不见了,看来她也是有份的。我们打开阿明的抽屉,发现了许多他和裕丽的做爱的照片,还有投稿到三级杂志哩!有些照片的女主角样子很像是妳,不过我知道不会是真的!”
我一口否定,随即便躲进厨房里去,两手掩著两行遏止不住的泪水,忍着哭声,不让我丈夫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