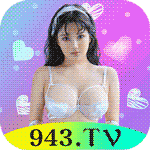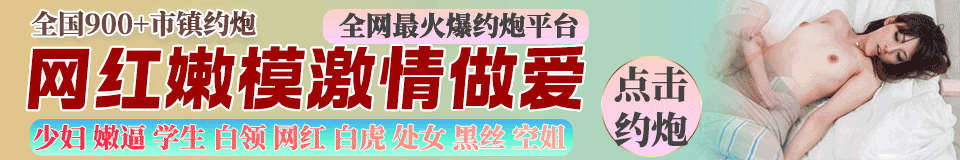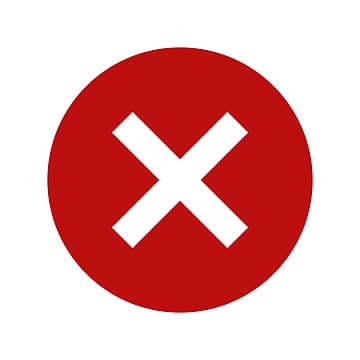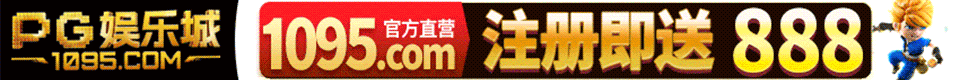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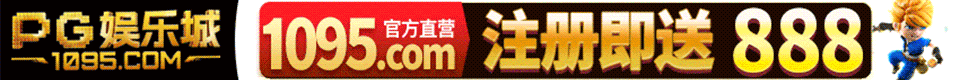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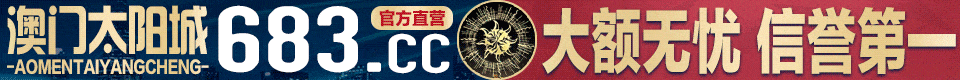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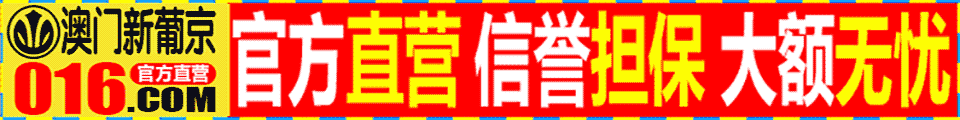














诱人小姨学电脑学上床
我名叫谭祥,十六岁,我有一个美小姨叫嘉美,我叫她嘉美姨。
嘉美姨是我妈妈的妹妹,她的职业是模特儿,她十四岁时被街上的星探发掘,初出道时她已经担任动漫女郎,早在第一代高达动画和模型出现时,她经常出席不同的模型展,动漫节中担当角色扮演的模特儿,她以穿驾驶服的马茜、军官服的花拉或娜娜造型,穿着机动战士联邦军制服,作为招俫。
嘉美姨样貌标致(七分像新闻报导员周嘉仪,三分像桂仑美),身裁不俗是C-CUP人马(对于当时未有波霸的观念出现时,嘉美姨的身裁已经十分劲爆)再加上一对修长美腿,尤其那个年代的女性十分喜欢穿丝袜。可以说是十分动人。
因为对漂亮的嘉美姨来说,因为赚钱容易,高中未读完,便已经辍学。用其姣好身裁和容貌走上时装天桥。曾经是红过一段短时候,但敌不过新晋的模特儿,什么陈嘉容,周汶锜等。早期的模特儿,很少报章杂志报导,浮浮沈沈半红不黑多年。最终二十五岁时,搭上了一位风流的太子爷,闪电结婚,外婆和妈妈根本不看好这段婚姻,果然不到两三年,娱乐版报导那太子爷外间包养数名女星,嘉美姨一气之下便跑回娘家。
离婚后的嘉美姨那年已经廿八岁,身裁和容貌还算保养得好。但曾经嫁作冯妇的女人,要再走上天桥并不容易,就算回去做动漫女郎,岁月的痕迹根本不容许她与那些青春诱人的什么动漫MAGGIE,和新晋电视姐仔争一日之长短。
在二十世纪末期,嘉美姨可谓真正的三无,“无才,无学,无钱”。年轻时有钱乱花,无钱就賖借渡日。书又没有多读一点。
出外找工作,难过登天。
我爸爸总算是一间制衣厂的厂长,我妈便哄爸安排她在厂内帮手入单入资料等悠闲工作。
岂料她连电脑也不懂操作。
吃饭的时候,“祥仔,你明天是不是开始放暑假?”老爸开口道。
“唔!”我口里塞饭菜回应道。
“明天开始你教嘉美姨如何操作电脑好吗?”
“不要啦!嘉美姨是正统的电脑白痴!连电脑也会让她弄坏的!”
“她已经弄坏了公司的入数电脑了。我不能再让自己冒险放一个计时炸弹在身边。拜托啦!”爸爸苦恼的说
“我拜托你别拜托我啦!我最怕这种蠢女人的了”
“嘉美姨是你的长辈,别没大没小的说人家!”妈妈忍不住插上一口,“你不要忘了,以前你小时候嘉美姨对你多好呀!她有钱的时候,经常买糖、买玩具给你呀!”
“咸丰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说来说去,你这小子都是要有钱驶得鬼推磨,30元1小时。”还是老爸最了解我。
“40元,过三十分钟当一小时计。”
“你这臭小子,竟然跟爸爸计。好!就40元,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我跟爸爸一个五
所以我十六岁的那个暑假,便当上担任嘉美姨电脑教师一职,也失去了我的童贞。
第二天早上,家里父母都出外工作,打网络游戏至半夜的我,在床上被雨声和门铃声吵醒。
甫一打开门,只见嘉美姨全身湿漉漉,全身打颤的站在眼前。
白色的小背心已经紧贴著肌肤,连乳荤的型态都能隐若可见,裙脚紧贴著湿透的尼龙丝袜大腿,连袜裤缝线和内裤的颜色都辨认出来,是鲜黄色的。
可爱的脸庞上的发脚和流海还滴下水滴,真的一股冲动想把她抱到怀中。
“嘉美姨!”我顿时睁开着惺忪睡眼,伸手到背心下抓痒,“你怎么全身湿了?”
“今天我一早出门,忘了带雨伞。”她的眼睛望着那条四角骨内裤,因为早上,年少气盛的我,鸡巴当然是高昂翘首的撑起裤头。
“我知,但我不知道你会这么早?”我不好意思拿起咕臣遮挡着下体,打了一个呵欠。
“我想到浴室换件衣服。你可以帮我拿你妈妈的衣服给我好吗”她娇羞的说。
“你先到洗手间,我去给你拿衣服!”
我从妈妈的抽柜中拿出一件旧白色发黄的T裇,上面印有白雪公主粉红色的外廓。
我敲敲门,门扉微开。只见嘉美姨全身赤裸的在浴室中擦拭著湿透的头白,嘉美姨的身裁均称,乳房和臀部都坚挺结实,手臂高举露出光滑的下腋。
看得我喉干舌燥,这时嘉美姨也发现我的身影,我只好侧过面把衣服搋入洗手间内给嘉美姨,
“嘉美姨,我把妈妈的衣服放洗手盘上。”
“谢谢,慢著,祥仔,可以帮我拿一包你妈妈未开的袜裤给我吗?我全身都湿透了。
我含糊的应了一声,便跑到妈妈房里,在内衣物的柜子内,找到一包三元一包的爱美神牌肉色尼龙袜裤。
回到大厅时,只见嘉美姨坐在沙发上走出来微笑着望着我,天呀!是男性荷尔蒙还是费洛蒙作的怪吗?我竟然有一种心如鹿撞的感觉,嘉美姨明明穿的是妈妈套头T裇,但却比妈妈穿得漂亮何止十倍,化上淡粧,衫摆下露出一对雪白无毛的长腿,脚趾甲上涂上无色的指甲油,发出如珠贝的珍珠光。
我把袜裤搋给嘉美姨
嘉美姨拆开包,把幼滑的丝袜抽出,仔细的卷起袜筒,把小巧的脚掌套入,她竟打算在她的姨甥面前穿丝袜,丝袜一直从脚跟滑上小腿、膝盖,然后嘉美姨又穿上另一端,看得我的小弟差点儿胀爆。
正当她要把袜裤套上大腿时,“你不是要教我电脑的吗”
“对呀!嘉美姨,电脑在我的房间,你不介意到我房间吗?”
“我不介意!你先到房里准备一下,我很快进来。”
我回到房间,从门扉偷窥,只见嘉美姨把双手插入袜裤的筒子内,慢慢仔细地把袜裤套上大腿。让丝袜紧贴著大腿,然后再抽上了小腹,只见嘉美姨把袜裤的缝子调整至正中,隔着袜裤的小腹上竟有灰黑一片的耻毛渗出,原来嘉美姨全身湿透,索性连内裤也脱了下来。嘉美姨检查了自己那浑圆的屁股,是否没有走样后,便要步入我的房间。
我立时如“仙鹤神针”中的白云飞使出迷踪步一样,踏了几个圈,跳上了床上。
嘉美姨甫一进我凌乱的房间,连路也没有得走,
“请问我该怎么进来呢?”
“看着我!”我重新示范上床的动作。
“来吧!”赤足的嘉美姨只好仿效我一样,跳上床,坐在我身旁。我不禁多望她的长腿数眼。
“祥仔,我看你要收拾一下房间了。”
“你现在的身份是我的学生,有什么训话,下课后再说。”我装上老师的
“对不起,老师!”
“你先开电脑给我看看。”
她把萤光幕掣扭开了,她很自豪的说︰“开了。”
我差点儿滴汗,我叹了一口气︰“嘉美姨,她只是萤光幕的电源开关!不是电脑的电源开关”
“是吗!哈哈哈,我是不是很有幽默感呀!”尴尬的嘉美姨还在自圆其说。
我便开始如幼稚园手的捉她的柔荑教她如何开启电和使用鼠标时,从宽松的衣领处看见两只雪白坚挺的乳房,原来嘉美姨T裇内是真空处理。
嘉美姨的肌肤十分嫩滑,就好似丝绢般,身上还传来淡淡白兰花香水味。嗅得我唾液狂吞。
我教了嘉美姨如何进入微软的EXCEL,如何入数,嘉美姨也确实是用心学习,再加上一点小聪明,她已掌握了初步。
但不久嘉美姨双颊微红,全身抖颤起来。
“我好冷呀!”嘉美姨把我的被子盖在身上。
我见她抖得厉害,用手背一碰她的前额,热得烫手。
“嘉美姨,你发烧耶!”
“我好辛苦!”
“我们楼下有中医,要去看看吗?”
“不,中药很苦呢!你有西成药吗?”
“我去找找看吧!”
我走了去厨房放置的药箱中,找到一盒退烧感冒药,我知这成药的药力十分之猛,上次老爸吃了一颗,便睡了一整天。
我把水杯和药包拿进房时。
“唉唷!”嘉美姨一个跟斗跌在地上。
我立时把药包和水杯,先放在桌上,扶起嘉美姨,
“你的模型勾住我的丝袜了。”嘉美姨蹏起一脚,一根模型框子勾住了嘉美姨脚掌的丝袜。
“这些药是给我的吗?”
“对!”我太过专注把框子上的丝袜纤维拆下,忘了告诉她一声。我忍不住轻抚嘉美姨的美脚掌。
当我回头时,只见药包内有少了两片药片。
“你吃了两片吗?”我吓了一惊!
“对呀!”
“这药很猛的,一片已经教人睡上一天了。”
“别担心没事的。”
不出所料,不到十分钟,嘉美姨开始昏昏欲睡。
她正想喝口水提提神,竟把杯中水倒到身子和床上,
我去洗手间拿抹布时,发现嘉美姨的衣服挂在衣架上,雪白的乳罩和一条鲜黄色的棉质内裤还滴著水滴。望着那套内衣裤,我竟然产生出对嘉美姨的妄想来。
回来时,只见嘉美姨已经倒头于床上,发出微微鼾声。衬衣翻倒屁股上,连袜裤的裤头和屁眼都能清晰可见。
我轻轻推她,“嘉美姨,嘉美姨。”全无反应。
只见嘉美姨胸前一片湿透,乳房和乳头的形状颜色都清楚看见。
我抖著抺布,我绕到嘉美姨的背挨着她,把她身上衣服多余的水份抹去。
抹着抹著,抹布已经不在手上了,我的手已经搓揉着她一对糯软的乳房。
我还是一个处男,只是靠阅看“龙虎豹”(香港某著名色情杂),才学到皮毛的性知识。
我的裤裆紧顶着嘉美姨光滑的屁股,拚命磨弄着我的呼吸很粗糙。
我向嘉美姨的粉颈索吻,太赞了,女孩子的皮肤又嫩又滑。
我索性把自己的四角骨裤拉到膝盖下,把自己那粗胀的鸡巴,顶着隔着丝袜的屁眼(我当时还以为那儿是女性的阴道),那种幼滑的感觉令人爽死了。
我只有拚命的磨弄著。
“啊‥‥啊‥‥啊‥嘉美姨‥‥啊”下体一阵刺痛,那浓稠的精液如喷泉般从输精管激射出来,当我回过神时,只见几团白浊铺在嘉美姨的屁股上。
我怕被嘉美姨发现,我决定把她的袜裤和T裇一并脱掉,。
我又去妈妈的房间拿了一套干净的T裇和肉色袜裤,打算替嘉美姨换上时。
只见嘉美姨的裸体美艳地摊在我的床上,令我又立时冲动起来。
当替嘉美姨穿着袜裤时,只见她一丛耻毛下,一只如熟烂的蜜桃透出淡淡的甜香,看了很多色情小说的描述,知道这是阴阜,那些好色老头都是如夜袭自己的年轻媳妇,舐至她叫公公我要。
我便照办煮碗的舐刮嘉美姨那阴户,沈睡中的嘉美姨竟然起了反应,本来干涩的阴户,竟流出滑潺潺的蜜液,甜腻中带点咸香。
“唔‥啊‥‥‥唔‥”嘉美姨在睡梦中发出诱人的呻吟声。
我只好继续舐啜嘉美姨的美穴,阴唇也被我舐翻了,沈醉在绮梦中的嘉美姨更自动的张开两腿。
我只见阴唇翻开的小穴呈湿润的粉红色,令我忍不住把长茧的手指插入其内,小穴紧啜着我的手指。
当我拔出手指时,上面黏满了嘉美姨的爱液,我把手指放进口中把嘉美姨的爱液吞下,下体如同吃了威而钢一样,又翘又硬。
我把嘉美姨一条腿擡起,把硬直的鸡巴试图插入她的流水汨汨的小穴中,套弄了好几次,总算成功的将阳具插进去。嘉美姨的阴壁把我的鸡巴紧紧吸啜著。
免得自己一插入便早泄,我大力深呼吸了数下,才开始用力干嘉美姨,一抽一入的,我拚命干着嘉美姨,又怕她会醒过来。
嘉美姨的乳房真是美死了,一路插一路愰动着。
最后在紧急关头,我立时抽出喷精的阳具又弄污了嘉美姨的小腹。
当嘉美姨醒过来时,已经是下午三时多,身上当然穿了整齐的T裇和袜裤,我则继续打网上游戏。
嘉美的衣服也干透了,便嚷着肚子饿的出外吃饭。
那天晚上我拿着嘉美衣穿过的袜裤来打炮,差不多打了三发,才能让自己入睡。
我名叫谭祥,十六岁,我有一个美小姨叫嘉美,我叫她嘉美姨。
嘉美姨是我妈妈的妹妹,她的职业是模特儿,她十四岁时被街上的星探发掘,初出道时她已经担任动漫女郎,早在第一代高达动画和模型出现时,她经常出席不同的模型展,动漫节中担当角色扮演的模特儿,她以穿驾驶服的马茜、军官服的花拉或娜娜造型,穿着机动战士联邦军制服,作为招俫。
嘉美姨样貌标致(七分像新闻报导员周嘉仪,三分像桂仑美),身裁不俗是C-CUP人马(对于当时未有波霸的观念出现时,嘉美姨的身裁已经十分劲爆)再加上一对修长美腿,尤其那个年代的女性十分喜欢穿丝袜。可以说是十分动人。
因为对漂亮的嘉美姨来说,因为赚钱容易,高中未读完,便已经辍学。用其姣好身裁和容貌走上时装天桥。曾经是红过一段短时候,但敌不过新晋的模特儿,什么陈嘉容,周汶锜等。早期的模特儿,很少报章杂志报导,浮浮沈沈半红不黑多年。最终二十五岁时,搭上了一位风流的太子爷,闪电结婚,外婆和妈妈根本不看好这段婚姻,果然不到两三年,娱乐版报导那太子爷外间包养数名女星,嘉美姨一气之下便跑回娘家。
离婚后的嘉美姨那年已经廿八岁,身裁和容貌还算保养得好。但曾经嫁作冯妇的女人,要再走上天桥并不容易,就算回去做动漫女郎,岁月的痕迹根本不容许她与那些青春诱人的什么动漫MAGGIE,和新晋电视姐仔争一日之长短。
在二十世纪末期,嘉美姨可谓真正的三无,“无才,无学,无钱”。年轻时有钱乱花,无钱就賖借渡日。书又没有多读一点。
出外找工作,难过登天。
我爸爸总算是一间制衣厂的厂长,我妈便哄爸安排她在厂内帮手入单入资料等悠闲工作。
岂料她连电脑也不懂操作。
吃饭的时候,“祥仔,你明天是不是开始放暑假?”老爸开口道。
“唔!”我口里塞饭菜回应道。
“明天开始你教嘉美姨如何操作电脑好吗?”
“不要啦!嘉美姨是正统的电脑白痴!连电脑也会让她弄坏的!”
“她已经弄坏了公司的入数电脑了。我不能再让自己冒险放一个计时炸弹在身边。拜托啦!”爸爸苦恼的说
“我拜托你别拜托我啦!我最怕这种蠢女人的了”
“嘉美姨是你的长辈,别没大没小的说人家!”妈妈忍不住插上一口,“你不要忘了,以前你小时候嘉美姨对你多好呀!她有钱的时候,经常买糖、买玩具给你呀!”
“咸丰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说来说去,你这小子都是要有钱驶得鬼推磨,30元1小时。”还是老爸最了解我。
“40元,过三十分钟当一小时计。”
“你这臭小子,竟然跟爸爸计。好!就40元,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我跟爸爸一个五
所以我十六岁的那个暑假,便当上担任嘉美姨电脑教师一职,也失去了我的童贞。
第二天早上,家里父母都出外工作,打网络游戏至半夜的我,在床上被雨声和门铃声吵醒。
甫一打开门,只见嘉美姨全身湿漉漉,全身打颤的站在眼前。
白色的小背心已经紧贴著肌肤,连乳荤的型态都能隐若可见,裙脚紧贴著湿透的尼龙丝袜大腿,连袜裤缝线和内裤的颜色都辨认出来,是鲜黄色的。
可爱的脸庞上的发脚和流海还滴下水滴,真的一股冲动想把她抱到怀中。
“嘉美姨!”我顿时睁开着惺忪睡眼,伸手到背心下抓痒,“你怎么全身湿了?”
“今天我一早出门,忘了带雨伞。”她的眼睛望着那条四角骨内裤,因为早上,年少气盛的我,鸡巴当然是高昂翘首的撑起裤头。
“我知,但我不知道你会这么早?”我不好意思拿起咕臣遮挡着下体,打了一个呵欠。
“我想到浴室换件衣服。你可以帮我拿你妈妈的衣服给我好吗”她娇羞的说。
“你先到洗手间,我去给你拿衣服!”
我从妈妈的抽柜中拿出一件旧白色发黄的T裇,上面印有白雪公主粉红色的外廓。
我敲敲门,门扉微开。只见嘉美姨全身赤裸的在浴室中擦拭著湿透的头白,嘉美姨的身裁均称,乳房和臀部都坚挺结实,手臂高举露出光滑的下腋。
看得我喉干舌燥,这时嘉美姨也发现我的身影,我只好侧过面把衣服搋入洗手间内给嘉美姨,
“嘉美姨,我把妈妈的衣服放洗手盘上。”
“谢谢,慢著,祥仔,可以帮我拿一包你妈妈未开的袜裤给我吗?我全身都湿透了。
我含糊的应了一声,便跑到妈妈房里,在内衣物的柜子内,找到一包三元一包的爱美神牌肉色尼龙袜裤。
回到大厅时,只见嘉美姨坐在沙发上走出来微笑着望着我,天呀!是男性荷尔蒙还是费洛蒙作的怪吗?我竟然有一种心如鹿撞的感觉,嘉美姨明明穿的是妈妈套头T裇,但却比妈妈穿得漂亮何止十倍,化上淡粧,衫摆下露出一对雪白无毛的长腿,脚趾甲上涂上无色的指甲油,发出如珠贝的珍珠光。
我把袜裤搋给嘉美姨
嘉美姨拆开包,把幼滑的丝袜抽出,仔细的卷起袜筒,把小巧的脚掌套入,她竟打算在她的姨甥面前穿丝袜,丝袜一直从脚跟滑上小腿、膝盖,然后嘉美姨又穿上另一端,看得我的小弟差点儿胀爆。
正当她要把袜裤套上大腿时,“你不是要教我电脑的吗”
“对呀!嘉美姨,电脑在我的房间,你不介意到我房间吗?”
“我不介意!你先到房里准备一下,我很快进来。”
我回到房间,从门扉偷窥,只见嘉美姨把双手插入袜裤的筒子内,慢慢仔细地把袜裤套上大腿。让丝袜紧贴著大腿,然后再抽上了小腹,只见嘉美姨把袜裤的缝子调整至正中,隔着袜裤的小腹上竟有灰黑一片的耻毛渗出,原来嘉美姨全身湿透,索性连内裤也脱了下来。嘉美姨检查了自己那浑圆的屁股,是否没有走样后,便要步入我的房间。
我立时如“仙鹤神针”中的白云飞使出迷踪步一样,踏了几个圈,跳上了床上。
嘉美姨甫一进我凌乱的房间,连路也没有得走,
“请问我该怎么进来呢?”
“看着我!”我重新示范上床的动作。
“来吧!”赤足的嘉美姨只好仿效我一样,跳上床,坐在我身旁。我不禁多望她的长腿数眼。
“祥仔,我看你要收拾一下房间了。”
“你现在的身份是我的学生,有什么训话,下课后再说。”我装上老师的
“对不起,老师!”
“你先开电脑给我看看。”
她把萤光幕掣扭开了,她很自豪的说︰“开了。”
我差点儿滴汗,我叹了一口气︰“嘉美姨,她只是萤光幕的电源开关!不是电脑的电源开关”
“是吗!哈哈哈,我是不是很有幽默感呀!”尴尬的嘉美姨还在自圆其说。
我便开始如幼稚园手的捉她的柔荑教她如何开启电和使用鼠标时,从宽松的衣领处看见两只雪白坚挺的乳房,原来嘉美姨T裇内是真空处理。
嘉美姨的肌肤十分嫩滑,就好似丝绢般,身上还传来淡淡白兰花香水味。嗅得我唾液狂吞。
我教了嘉美姨如何进入微软的EXCEL,如何入数,嘉美姨也确实是用心学习,再加上一点小聪明,她已掌握了初步。
但不久嘉美姨双颊微红,全身抖颤起来。
“我好冷呀!”嘉美姨把我的被子盖在身上。
我见她抖得厉害,用手背一碰她的前额,热得烫手。
“嘉美姨,你发烧耶!”
“我好辛苦!”
“我们楼下有中医,要去看看吗?”
“不,中药很苦呢!你有西成药吗?”
“我去找找看吧!”
我走了去厨房放置的药箱中,找到一盒退烧感冒药,我知这成药的药力十分之猛,上次老爸吃了一颗,便睡了一整天。
我把水杯和药包拿进房时。
“唉唷!”嘉美姨一个跟斗跌在地上。
我立时把药包和水杯,先放在桌上,扶起嘉美姨,
“你的模型勾住我的丝袜了。”嘉美姨蹏起一脚,一根模型框子勾住了嘉美姨脚掌的丝袜。
“这些药是给我的吗?”
“对!”我太过专注把框子上的丝袜纤维拆下,忘了告诉她一声。我忍不住轻抚嘉美姨的美脚掌。
当我回头时,只见药包内有少了两片药片。
“你吃了两片吗?”我吓了一惊!
“对呀!”
“这药很猛的,一片已经教人睡上一天了。”
“别担心没事的。”
不出所料,不到十分钟,嘉美姨开始昏昏欲睡。
她正想喝口水提提神,竟把杯中水倒到身子和床上,
我去洗手间拿抹布时,发现嘉美姨的衣服挂在衣架上,雪白的乳罩和一条鲜黄色的棉质内裤还滴著水滴。望着那套内衣裤,我竟然产生出对嘉美姨的妄想来。
回来时,只见嘉美姨已经倒头于床上,发出微微鼾声。衬衣翻倒屁股上,连袜裤的裤头和屁眼都能清晰可见。
我轻轻推她,“嘉美姨,嘉美姨。”全无反应。
只见嘉美姨胸前一片湿透,乳房和乳头的形状颜色都清楚看见。
我抖著抺布,我绕到嘉美姨的背挨着她,把她身上衣服多余的水份抹去。
抹着抹著,抹布已经不在手上了,我的手已经搓揉着她一对糯软的乳房。
我还是一个处男,只是靠阅看“龙虎豹”(香港某著名色情杂),才学到皮毛的性知识。
我的裤裆紧顶着嘉美姨光滑的屁股,拚命磨弄着我的呼吸很粗糙。
我向嘉美姨的粉颈索吻,太赞了,女孩子的皮肤又嫩又滑。
我索性把自己的四角骨裤拉到膝盖下,把自己那粗胀的鸡巴,顶着隔着丝袜的屁眼(我当时还以为那儿是女性的阴道),那种幼滑的感觉令人爽死了。
我只有拚命的磨弄著。
“啊‥‥啊‥‥啊‥嘉美姨‥‥啊”下体一阵刺痛,那浓稠的精液如喷泉般从输精管激射出来,当我回过神时,只见几团白浊铺在嘉美姨的屁股上。
我怕被嘉美姨发现,我决定把她的袜裤和T裇一并脱掉,。
我又去妈妈的房间拿了一套干净的T裇和肉色袜裤,打算替嘉美姨换上时。
只见嘉美姨的裸体美艳地摊在我的床上,令我又立时冲动起来。
当替嘉美姨穿着袜裤时,只见她一丛耻毛下,一只如熟烂的蜜桃透出淡淡的甜香,看了很多色情小说的描述,知道这是阴阜,那些好色老头都是如夜袭自己的年轻媳妇,舐至她叫公公我要。
我便照办煮碗的舐刮嘉美姨那阴户,沈睡中的嘉美姨竟然起了反应,本来干涩的阴户,竟流出滑潺潺的蜜液,甜腻中带点咸香。
“唔‥啊‥‥‥唔‥”嘉美姨在睡梦中发出诱人的呻吟声。
我只好继续舐啜嘉美姨的美穴,阴唇也被我舐翻了,沈醉在绮梦中的嘉美姨更自动的张开两腿。
我只见阴唇翻开的小穴呈湿润的粉红色,令我忍不住把长茧的手指插入其内,小穴紧啜着我的手指。
当我拔出手指时,上面黏满了嘉美姨的爱液,我把手指放进口中把嘉美姨的爱液吞下,下体如同吃了威而钢一样,又翘又硬。
我把嘉美姨一条腿擡起,把硬直的鸡巴试图插入她的流水汨汨的小穴中,套弄了好几次,总算成功的将阳具插进去。嘉美姨的阴壁把我的鸡巴紧紧吸啜著。
免得自己一插入便早泄,我大力深呼吸了数下,才开始用力干嘉美姨,一抽一入的,我拚命干着嘉美姨,又怕她会醒过来。
嘉美姨的乳房真是美死了,一路插一路愰动着。
最后在紧急关头,我立时抽出喷精的阳具又弄污了嘉美姨的小腹。
当嘉美姨醒过来时,已经是下午三时多,身上当然穿了整齐的T裇和袜裤,我则继续打网上游戏。
嘉美的衣服也干透了,便嚷着肚子饿的出外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