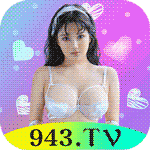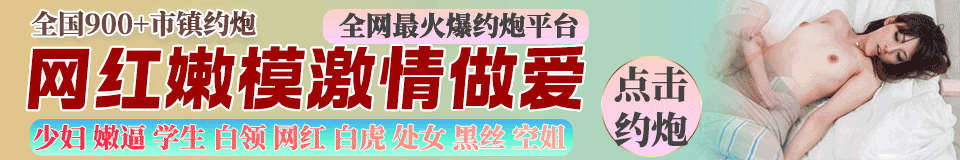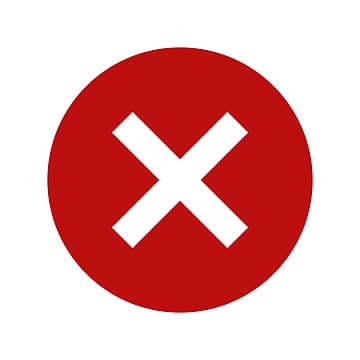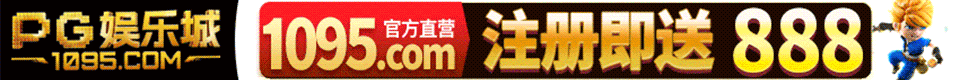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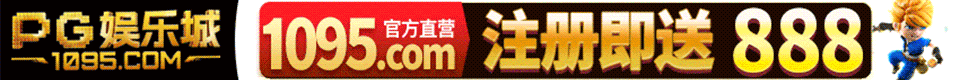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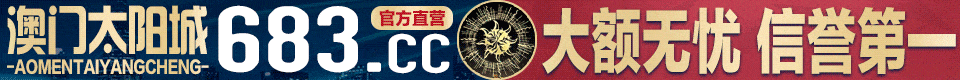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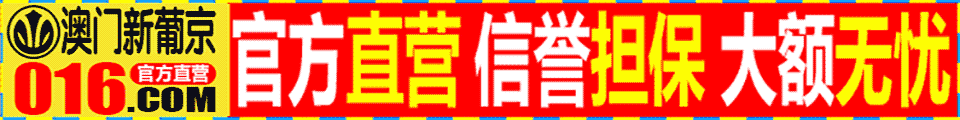














我的媽媽白玉貞
(上)
當秋日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入臥室,我就從夢中醒來了,把手伸進褲頭裏調整了一下因為晨勃而硬挺的肉棒,這才慢悠悠從床上坐了起來,身邊的被窩裏還殘留著伊人的體溫和香氣,這意味著她才剛離開不久……
我叫李慕白,這名字據說是爺爺當時請教了一個過路的算命先生給取的,至于真假,我也無法得知,爺爺在我出生之前就葬在了後山的一個小山包裏頭了。父親是李樹牛,小學畢業的他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工,一年到頭都在外面打拼,到了農忙時節或者是大年三十我才得以見他一面。因為我是家中獨子,生下來就備受家裏人疼愛。因為今年高考失利,所以打算復讀爭取到來年考個一本,這才對得起家裏的期望啊。我生在是南方的一個小村莊,這裏依舊貧窮落後,這裏的人世世代代都依靠著家裏的一畝三分地生活著。可我家裏窮歸窮,老爸出去打拼的這些年還是得了不少積蓄,在村子裏蓋起的這棟兩層高的樓房,倒也讓不少同村的人們艷羨稱贊。也因此,不少寡漢都跟著我父親出去打工了,留下大半個村子的婦孺老人,大片的田地就這麽荒廢了。
我媽媽白玉貞是被父親從外面買回來的,這件事在村子裏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了。而前面說到的那些願意跟著我父親出去打工的寡漢大多都是衝著這個去的,他們渴望女人,都奢望著過年的時候能夠買到一個像我媽媽這般水靈白嫩的老婆回家,白天一起生活,晚上關了門脫了褲子就能操個爽。
媽媽白玉貞,一個來自廣陵的女人,十七歲那年被壞人從回家的公車上迷暈並拐賣到了南方,後來就被我父親李樹牛花了五千塊錢從人販子手裏買了過來,再後來,就生下了我。這些年來,她不是沒有想過要逃回家去,也就是在生下我之後的某個夜裏趁著我父親睡著了,她拿出白天就收拾好的衣裹悄悄開了門就逃了,結果被村裏的一個守山豬的大叔發現了,我那些個叔伯帶著我父親就打著燈火追上去給抓了回來。陸陸續續有了那麽幾回,挨了打吃了痛的她知道逃不掉了就不逃了。父親老實,雖說對她的幾次出逃心存芥蒂,但說到底對她還算是好的,家裏的好吃的都給了她,新買的衣裳也是她的,除了限制其自由,哪裏都沒有虧待她。她慢慢沒了唸頭,就真的住下了,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自我懂事起,我就很少見得媽媽在人前笑起來的樣子,她衹會和我呆在一起的時候才放開地笑。她笑起來真的很美,尤其是那雙眼睛,水汪汪的,笑起來會彎成兩月牙。
這雁丘村的確稱得上是窮山惡水,可絲毫改變不了媽媽。三十多歲的她沒有像那些個山野村婦一般被太陽曬傷了皮膚,白嫩的臉蛋總會讓人懷疑她的歲數,平日裏的言行舉止都透露著江南一帶的婉約端莊,家裏挂著的旗袍就更與她們不同,但媽媽衹有在過節的時候才會穿在身上。又因為在哺乳期得到了充足的能量補充,喝了不少中草藥湯的媽媽那時還尚且青澀的胸部不僅僅奶水充足,還完美發育,鼓脹豐滿的雙峰幾乎要撐破胸衣,這就足以傲視村裏大半婦人,而且安心在這住下的她還注重保養,盡管歲數在改變,身材與胸型卻依舊保持著巔峰狀態,將近一米七的身材,凹凸有致,真真羨慕死那些大媽大嬸。
第一次接觸亂倫,是我讀初中的時候。
那天,我去給同學送資料。因為路程有點遠,我特意提前了半個小時出門,等渾身汗水的我趕到鄰村同學家裏時,也才過了十五分鐘。我把自行車鎖在他門口,因為私下感情好,所以平日來往多次都沒有敲門,這次也不例外,可當我推門進去想要跟同學打招呼的時候,就發現事情變得不簡單了。我聽見了女人的呻吟聲,像極了那些A 片中的女優的淫叫,一開始還以為那家夥在家看毛片,後來仔細想想不對勁兒,因為我們平日在學校偷看毛片時都得戴著耳機躲進廁所裏頭,哪有這麽大膽開著外放?更何況在家看的話,不也都是等著家裏人睡下了才悄悄的打開帶著耳機把自己隱藏的好好的?
當時也是膽邊長了毛,我竟然偷偷循著女人的呻吟摸了過去,這裏來過太多次了,以至于我對這裏的布置了如指掌。很快,我就摸到了同學父母的臥室外邊,而聲音就從裏面傳出來。
是同學的父母?
我心裏想著,可很快就否定了。因為他的爸爸常年在外經商,回家次數比我父親還少,怎麽可能會在這個季節回來?
那會是誰?
我見房門未鎖,就偷偷伸頭去看,結果看到了讓我震驚的一幕。
我同學和他的媽媽兩個人赤裸裸的在床上翻滾著,白花花的肉體糾纏在一起,然後同學重重地在他媽媽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就看見他媽媽順從地跪在床上撅起雪白的屁股,擺出一個羞恥的姿勢,同學見狀就笑出聲來扶著肉棒慢慢湊近,然後狠狠一挺,她媽媽就仰起頭來大聲的叫了起來。同學插的越恨,他媽媽叫的越浪,什麽親丈夫,什麽大雞巴兒子,統統都喊了出來,也幸虧這裏住的人都隔了些距離,不然肯定能夠聽見。我在門外看得是唇幹舌燥,雞兒硬邦邦的,完全沒有想到平日裏斯斯文文的同學居然會把雞巴插進他媽媽的身體裏,更沒有想到他那個平日裏優雅端莊的老師媽媽在床上居然會是這般放蕩淫亂。
我不知道他們在我到來之前做了多久,反正我在外面站著看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換著姿勢,聽著他們母子間淫蕩的對話,最後親眼目睹同學內射他那個淫蕩的母親後一股濃精從那個鮮紅的陰唇間流出來,這個過程足足持續了十五分鐘。
「小母狗,快起來!再過一會兒,我同學就來了,讓他看見妳這幅模樣,我可就慘了!」
衹見同學「啪」的一巴掌扇在他媽媽的奶子上,鮮紅的掌印立馬就浮現,可正含著兒子的肉棒的她竟然興奮的叫出聲來,我分明看見她那張開的大腿之間鮮紅的陰唇一陣收縮。
「還是說,妳想讓更多的人操妳?」
我同學捏著他媽媽的臉頰,惡狠狠地盯著她,然後又狠狠的將她摔在被汗水浸透的床榻上。
我見同學從床上下來找衣服穿上,就趕緊跑了。出了門,開了自行車,我就拼命往家裏跑。
最後,這次的送資料因為我的爽約而落空了。
同學不知道的是,那個晚上,我把他那個漂亮的老師媽媽當做了性幻想的對象,狠狠地射了一次又一次……
後來,等到初中畢業那天,同學拉著我到學校的天臺上吹風,在掏出一根煙遞給我後,叼著煙跟我說他其實知道那天我在他家裏,因為他聽見了我慌亂出門時弄出的聲響。我拿著他的煙不敢點著,最後跟他承諾不會向任何人說起這件事。在我正準備離去的時候,他伸手把我攔了下來,狠狠地抽了一口煙後就帶上我去了他家。那天,我倆在他那個騷浪的老師媽媽身上折騰了足足一個下午,除了開始幾次內射在他媽媽嬌嫩的肉屄裏頭,往後都射在她的身上,直到把她雪白的胴體都射滿了精液。那次之後,他們一家就搬走了……
真正的亂倫發生在去年的春節。
我記得很清楚,直到除夕那天下午,父親才從外地趕回家裏,手裏提著幾大袋煙酒和各種食品的他意氣風發,走路都帶風,衹因為他當上了包工頭,每個月能拿到比以往多雙倍的工資。
晚上,父親破例地在飯桌上讓我喝了酒,不僅如此,他還讓媽媽穿上了新買的大紅色鏤花金絲旗袍,以及那雙紅色的高跟鞋。媽媽沒說話,一一照做,還花了淡妝,梳了個漂亮的發髻。
一頓飯下來,在此之前從沒喝過酒的我在父親的勸說下喝了差不多半瓶紅酒,而他則喝得爛醉。我和媽媽好不容易才把他服侍睡下,這個過程母子倆少不了身體接觸。
半夜,酒醒的我感到口幹起來喝水,經過父母房間的時候聽到了他們做愛的聲音。其實,我每年都會聽見,可這次短短的兩分鐘卻讓我有了性衝動。
高中以來,不,應該是初中畢業那天後,我就對性愛產生了迷戀,時不時就會通過看黃書或者黃色碟片來打手槍。到縣城唸高中,我又接觸了電腦,以及電腦裏五花八門的網址,從一開始的小心嘗試,到最後的極度迷戀沈淪,衹用了短短的幾個通宵。從一開始的都市情色,到武俠玄幻,最後是母子亂倫,我一步步地走向罪惡的深淵,無法自拔。每次看著手機裏的亂倫小說和影片,每次在床上被窩裏的激情發射,我都沒有把媽媽作為性幻想對象,直到那天晚上我看到換上旗袍穿著高跟鞋的媽媽想起了初中畢業那天同學在我最後一次在他媽媽身上射進後說的話。
「妳媽媽那麽美,妳小子就不想搞她?」
黑暗中,父親很快就結束了,又掙紮著拖了幾分鐘,這才從媽媽身上滾下來。依稀可見的是而此時的媽媽雲鬢淩亂,身上甚至還穿著那身旗袍,輕輕嘆息一聲後就從床上下來,我知道她是要去洗澡了。
忍住渴意的我躲在轉角裏看著穿著高跟鞋的媽媽從房間裏出來,往我臥室的方向看了看後就走向浴室,她應該是怕我聽到動靜,卻壓根沒有想到我早就躲在不遠處窺看著她。
然而媽媽沒有直接去浴室,而是進了廁所。我偷摸著跟上去躲在門外聽見她用紙巾擦拭的聲音,一個勁兒的吞著唾液。她一定是在擦著父親射出來的東西!
我一邊幻想著媽媽在裏面的動作,一邊脫下褲子掏出了肉棒,正要開始擼管,卻聽見媽媽的聲音從裏面傳了出來。
「誰?誰在外面?」她的聲音發顫,應該是太緊張了。
我知道是自己剛才的動作太大了,所以驚擾了媽媽,趕緊說道,「媽媽,是我,慕白啊!」
「啊!是……是妳啊?妳怎麽……怎麽還沒睡啊?」媽媽一聽到是我,就更加更緊張了,我都能聽見她慌亂地把紙巾揉成一團扔進馬桶的聲音了。
「我……我被尿憋醒了,所以起來解決一下。」我胡亂地找了個借口,「媽媽妳在方便嗎?」
「啊~是……是的!」大概是沒想到會發生這種尷尬的事情,媽媽一時竟有些語無倫次,「要……要不,妳去屋外?」
我哪裏肯輕易放過這難得的機會,連忙說道,「不不不!我能忍住,媽媽妳先解決吧!我在外面等一會兒就好了,再說了外面又黑又冷了,我最怕黑了!」
「那……那好吧!」媽媽居然還答應了!
就這樣,我站在廁所門外,媽媽躲在廁所裏面,僅有一門之隔。
足足有三分鐘,我都沒有聽見一點兒聲響,整個空間靜悄悄的。
「小白……要不……要不妳先?媽媽……媽媽……」後面的內容太羞人了,媽媽說不出口。
我不客氣的「嗯」的一聲,其實心中早有他想!
「咔!」廁所的門被打開了一條縫,緊接著是更多的,更多的!
我握著硬脹的肉棒,雙眼死死盯著慢慢打開的門縫,直到媽媽完全出現在門後。
「啊!」
看到門外的我的模樣,媽媽直嚇得尖叫!
我趁機向前,一手擋住她要關上的門,一手捂住她的嘴巴。
媽媽驚恐萬狀,雙手用力掰著我的手,雙目除了驚訝更多的是慌亂。
我用力擠進狹窄的廁所,然後反手關上門,隨後將媽媽推坐在馬桶上,捂住她嘴巴的手絲毫不敢放鬆。
「媽媽,我……我想……」我舔著幹幹的嘴唇,喘著粗氣說道,「我想……」
心知即將會發生什麽的媽媽「嗚嗚」地用力搖著頭,眼神透露著哀求,雙手用力地往外推著我的身體。
精蟲上腦的我開始懇求她,「就一次!就這一次!」
「嗚嗚!嗚嗚!」媽媽依舊搖頭,眼裏的淚水已經流了下來,然後就被我的手掌截住。
「一次都不可以嗎?我衹要一次就夠了啊!」
我幾乎崩潰,肉棒已經硬到要爆了,再不發泄,恐怕就要廢了。
「嗚嗚嗚嗚!」媽媽雙手合抱在一起,不停的向我求饒,小腦袋左右搖晃著,笑起來很好看的眼睛流出了更多的淚水。
我無視了她的哀求,抱住她的腰將她拉近,然後鬆開手,在她喊出聲來之前就吻住了她的嘴唇。媽媽並不配合,左右搖晃著腦袋,被我壓在胸前的雙手更加用力的推著我的胸膛,整個身軀都在扭動掙紮,這無疑更加激發了我的獸性!
我一手摟住媽媽,一手直接從旗袍高叉處伸進去胡亂掏摸,沒想到的是她沒有穿內褲!大腿的肌膚溫暖而滑嫩,沾染了父親的精液以及她自身的體液的陰毛貼在陰阜上,我的手指在那裏亂戳了幾下,就找到了生我出來的甬道!手指藉著那些體液順利插入媽媽小屄的時候,媽媽渾身一顫,「嗚嗚」地叫的更響了。
「妳看,妳那裏都濕了!是爸爸的精液還是妳的淫水?妳一定很想要了吧!」我用言語羞辱著媽媽,手指卻沒有停止動作,不停地扣弄著媽媽的屄肉,然後感受著她在我懷裏不停的顫抖,就會獲得莫名的快感!
母子倆就保持著這樣的姿勢,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裏開展了持久的拉鋸戰。
我的手指深入到媽媽的體內,那裏面很暖很滑,待會兒插進去一定很爽!一想到這裏,我就更加賣力的扣弄,直接就伸進去兩根手指,我要把父親的精液都掏幹凈!
「唔?嗚嗚!嗚嗚嗚嗚!」
突然,媽媽整個人都開始劇烈地扭動起來,一雙大腿左右搖晃,最後猛地一夾,發出長長的「嗚」的一聲,本來還在推著我胸膛的手臂就沒了力氣。
她高潮了!
我插入媽媽體內的手指感覺到一股暖流衝了出來,趕緊就把手指抽了出來,緊接著就是「嘩啦啦」的水聲,濺在我腿上的也不知道是尿還是媽媽的淫水。
我抱著渾身癱軟的媽媽,終于沒有再去封住她的嘴巴,因為她已經暈了過去。
我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所以衹能緊緊地抱著她,感受到她高低起伏的胸部,才稍稍安下心來。
然而,忍不住慾望的我還是撩起她的旗袍,一手扶住她的身體,一手握著肉棒慢慢向她靠近。
龜頭已經感覺到陰毛的存在了,衹需要用力一插,就能完完全全的進入到媽媽的體內。可我並沒有這樣做,衹是握著肉棒不停的磨蹭著媽媽的陰唇,單單是這樣的接觸,我就差點忍不住要射了!
這是我的親生媽媽啊!
小說和毛片裏頭的母子亂倫,那都是假的,這可真的是我的媽媽啊!生我養我的親生媽媽啊!
我一想到這,就難免心血澎湃,呼吸急促,握著肉棒的手都止不住顫抖了。
「嗯~」
媽媽終于醒了,慢悠悠的睜開眼睛,吐出了一口濁氣。
「媽媽?」我輕聲叫道,卻在下一秒捂住了她要喊出聲來的嘴巴,「噓!不要激動!萬一驚醒了爸爸,妳我可就慘咯!」
一聽到我提起父親,媽媽的情緒就更加激動了,再次掙紮起來。
我閉上眼睛,感受著龜頭處傳來的快感,笑出了聲。
媽媽這時才察覺到異樣,自己兩腿間有根火熱的東西正頂著自己的私密處,每一次的扭動,陰唇都會擦過那個粗碩的圓圓的頭部,身為人妻的她深知那是什麽,不正正就是眼前這個禽獸兒子的龜頭嗎!看著兒子無比享受的表情,她再次流下了屈辱哦的淚水,身體也不再胡亂扭動。
媽媽一停下來,我就睜開了眼睛,看著她哀求的神情,笑了笑說,「媽媽,舒服嗎?」
媽媽潮紅的臉蛋分不清是汗水還是眼淚,衹是一次又一次的搖著頭,發出「嗚嗚」的哀求聲。
「更舒服的在後面呢!」我邪惡的笑了笑。
用力將媽媽摟緊,我完全不用任何輔助就用龜頭叩開了回家的大門,兩片陰唇被龜頭狠狠地分開,緊接著就是用力的,插入!
「嗯!!!」
媽媽睜大眼睛,死死地盯著我,帶著恨意的眼神極其尖銳冰冷,最終卻還是被性起的我無視掉。
長十二公分的肉棒一插到底,滑嫩的肉壁被強硬撐開,敏感的龜頭撞在了一處更加柔軟的地方,幾乎是同一瞬間,我和媽媽都感覺到有一股電流擊穿了彼此的身體。
「啊!」
我激動得大叫出來,衹感覺三魂七魄都離開了身體,整個人都輕飄飄的,腦海裏一片空白!再低頭看媽媽,哦,她又暈了過去。
就這樣,我開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性愛之行——在這個狹小的廁所裏,我射出了人生中最猛最急也最多的一次!
當我把肉棒從媽媽高潮中的陰道裏抽出來時,那些白花花的濃精混合著媽媽的淫水一個勁兒的往外湧出,地板上積聚了一大灘這樣的混合液……
占有了這樣的尤物,我很快就重振了旗鼓。肉棒再次插入媽媽的小穴裏,我將她抱了起來,離開了廁所,向我的臥室走去。
(上)
當秋日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入臥室,我就從夢中醒來了,把手伸進褲頭裏調整了一下因為晨勃而硬挺的肉棒,這才慢悠悠從床上坐了起來,身邊的被窩裏還殘留著伊人的體溫和香氣,這意味著她才剛離開不久……
我叫李慕白,這名字據說是爺爺當時請教了一個過路的算命先生給取的,至于真假,我也無法得知,爺爺在我出生之前就葬在了後山的一個小山包裏頭了。父親是李樹牛,小學畢業的他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工,一年到頭都在外面打拼,到了農忙時節或者是大年三十我才得以見他一面。因為我是家中獨子,生下來就備受家裏人疼愛。因為今年高考失利,所以打算復讀爭取到來年考個一本,這才對得起家裏的期望啊。我生在是南方的一個小村莊,這裏依舊貧窮落後,這裏的人世世代代都依靠著家裏的一畝三分地生活著。可我家裏窮歸窮,老爸出去打拼的這些年還是得了不少積蓄,在村子裏蓋起的這棟兩層高的樓房,倒也讓不少同村的人們艷羨稱贊。也因此,不少寡漢都跟著我父親出去打工了,留下大半個村子的婦孺老人,大片的田地就這麽荒廢了。
我媽媽白玉貞是被父親從外面買回來的,這件事在村子裏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了。而前面說到的那些願意跟著我父親出去打工的寡漢大多都是衝著這個去的,他們渴望女人,都奢望著過年的時候能夠買到一個像我媽媽這般水靈白嫩的老婆回家,白天一起生活,晚上關了門脫了褲子就能操個爽。
媽媽白玉貞,一個來自廣陵的女人,十七歲那年被壞人從回家的公車上迷暈並拐賣到了南方,後來就被我父親李樹牛花了五千塊錢從人販子手裏買了過來,再後來,就生下了我。這些年來,她不是沒有想過要逃回家去,也就是在生下我之後的某個夜裏趁著我父親睡著了,她拿出白天就收拾好的衣裹悄悄開了門就逃了,結果被村裏的一個守山豬的大叔發現了,我那些個叔伯帶著我父親就打著燈火追上去給抓了回來。陸陸續續有了那麽幾回,挨了打吃了痛的她知道逃不掉了就不逃了。父親老實,雖說對她的幾次出逃心存芥蒂,但說到底對她還算是好的,家裏的好吃的都給了她,新買的衣裳也是她的,除了限制其自由,哪裏都沒有虧待她。她慢慢沒了唸頭,就真的住下了,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自我懂事起,我就很少見得媽媽在人前笑起來的樣子,她衹會和我呆在一起的時候才放開地笑。她笑起來真的很美,尤其是那雙眼睛,水汪汪的,笑起來會彎成兩月牙。
這雁丘村的確稱得上是窮山惡水,可絲毫改變不了媽媽。三十多歲的她沒有像那些個山野村婦一般被太陽曬傷了皮膚,白嫩的臉蛋總會讓人懷疑她的歲數,平日裏的言行舉止都透露著江南一帶的婉約端莊,家裏挂著的旗袍就更與她們不同,但媽媽衹有在過節的時候才會穿在身上。又因為在哺乳期得到了充足的能量補充,喝了不少中草藥湯的媽媽那時還尚且青澀的胸部不僅僅奶水充足,還完美發育,鼓脹豐滿的雙峰幾乎要撐破胸衣,這就足以傲視村裏大半婦人,而且安心在這住下的她還注重保養,盡管歲數在改變,身材與胸型卻依舊保持著巔峰狀態,將近一米七的身材,凹凸有致,真真羨慕死那些大媽大嬸。
第一次接觸亂倫,是我讀初中的時候。
那天,我去給同學送資料。因為路程有點遠,我特意提前了半個小時出門,等渾身汗水的我趕到鄰村同學家裏時,也才過了十五分鐘。我把自行車鎖在他門口,因為私下感情好,所以平日來往多次都沒有敲門,這次也不例外,可當我推門進去想要跟同學打招呼的時候,就發現事情變得不簡單了。我聽見了女人的呻吟聲,像極了那些A 片中的女優的淫叫,一開始還以為那家夥在家看毛片,後來仔細想想不對勁兒,因為我們平日在學校偷看毛片時都得戴著耳機躲進廁所裏頭,哪有這麽大膽開著外放?更何況在家看的話,不也都是等著家裏人睡下了才悄悄的打開帶著耳機把自己隱藏的好好的?
當時也是膽邊長了毛,我竟然偷偷循著女人的呻吟摸了過去,這裏來過太多次了,以至于我對這裏的布置了如指掌。很快,我就摸到了同學父母的臥室外邊,而聲音就從裏面傳出來。
是同學的父母?
我心裏想著,可很快就否定了。因為他的爸爸常年在外經商,回家次數比我父親還少,怎麽可能會在這個季節回來?
那會是誰?
我見房門未鎖,就偷偷伸頭去看,結果看到了讓我震驚的一幕。
我同學和他的媽媽兩個人赤裸裸的在床上翻滾著,白花花的肉體糾纏在一起,然後同學重重地在他媽媽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就看見他媽媽順從地跪在床上撅起雪白的屁股,擺出一個羞恥的姿勢,同學見狀就笑出聲來扶著肉棒慢慢湊近,然後狠狠一挺,她媽媽就仰起頭來大聲的叫了起來。同學插的越恨,他媽媽叫的越浪,什麽親丈夫,什麽大雞巴兒子,統統都喊了出來,也幸虧這裏住的人都隔了些距離,不然肯定能夠聽見。我在門外看得是唇幹舌燥,雞兒硬邦邦的,完全沒有想到平日裏斯斯文文的同學居然會把雞巴插進他媽媽的身體裏,更沒有想到他那個平日裏優雅端莊的老師媽媽在床上居然會是這般放蕩淫亂。
我不知道他們在我到來之前做了多久,反正我在外面站著看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換著姿勢,聽著他們母子間淫蕩的對話,最後親眼目睹同學內射他那個淫蕩的母親後一股濃精從那個鮮紅的陰唇間流出來,這個過程足足持續了十五分鐘。
「小母狗,快起來!再過一會兒,我同學就來了,讓他看見妳這幅模樣,我可就慘了!」
衹見同學「啪」的一巴掌扇在他媽媽的奶子上,鮮紅的掌印立馬就浮現,可正含著兒子的肉棒的她竟然興奮的叫出聲來,我分明看見她那張開的大腿之間鮮紅的陰唇一陣收縮。
「還是說,妳想讓更多的人操妳?」
我同學捏著他媽媽的臉頰,惡狠狠地盯著她,然後又狠狠的將她摔在被汗水浸透的床榻上。
我見同學從床上下來找衣服穿上,就趕緊跑了。出了門,開了自行車,我就拼命往家裏跑。
最後,這次的送資料因為我的爽約而落空了。
同學不知道的是,那個晚上,我把他那個漂亮的老師媽媽當做了性幻想的對象,狠狠地射了一次又一次……
後來,等到初中畢業那天,同學拉著我到學校的天臺上吹風,在掏出一根煙遞給我後,叼著煙跟我說他其實知道那天我在他家裏,因為他聽見了我慌亂出門時弄出的聲響。我拿著他的煙不敢點著,最後跟他承諾不會向任何人說起這件事。在我正準備離去的時候,他伸手把我攔了下來,狠狠地抽了一口煙後就帶上我去了他家。那天,我倆在他那個騷浪的老師媽媽身上折騰了足足一個下午,除了開始幾次內射在他媽媽嬌嫩的肉屄裏頭,往後都射在她的身上,直到把她雪白的胴體都射滿了精液。那次之後,他們一家就搬走了……
真正的亂倫發生在去年的春節。
我記得很清楚,直到除夕那天下午,父親才從外地趕回家裏,手裏提著幾大袋煙酒和各種食品的他意氣風發,走路都帶風,衹因為他當上了包工頭,每個月能拿到比以往多雙倍的工資。
晚上,父親破例地在飯桌上讓我喝了酒,不僅如此,他還讓媽媽穿上了新買的大紅色鏤花金絲旗袍,以及那雙紅色的高跟鞋。媽媽沒說話,一一照做,還花了淡妝,梳了個漂亮的發髻。
一頓飯下來,在此之前從沒喝過酒的我在父親的勸說下喝了差不多半瓶紅酒,而他則喝得爛醉。我和媽媽好不容易才把他服侍睡下,這個過程母子倆少不了身體接觸。
半夜,酒醒的我感到口幹起來喝水,經過父母房間的時候聽到了他們做愛的聲音。其實,我每年都會聽見,可這次短短的兩分鐘卻讓我有了性衝動。
高中以來,不,應該是初中畢業那天後,我就對性愛產生了迷戀,時不時就會通過看黃書或者黃色碟片來打手槍。到縣城唸高中,我又接觸了電腦,以及電腦裏五花八門的網址,從一開始的小心嘗試,到最後的極度迷戀沈淪,衹用了短短的幾個通宵。從一開始的都市情色,到武俠玄幻,最後是母子亂倫,我一步步地走向罪惡的深淵,無法自拔。每次看著手機裏的亂倫小說和影片,每次在床上被窩裏的激情發射,我都沒有把媽媽作為性幻想對象,直到那天晚上我看到換上旗袍穿著高跟鞋的媽媽想起了初中畢業那天同學在我最後一次在他媽媽身上射進後說的話。
「妳媽媽那麽美,妳小子就不想搞她?」
黑暗中,父親很快就結束了,又掙紮著拖了幾分鐘,這才從媽媽身上滾下來。依稀可見的是而此時的媽媽雲鬢淩亂,身上甚至還穿著那身旗袍,輕輕嘆息一聲後就從床上下來,我知道她是要去洗澡了。
忍住渴意的我躲在轉角裏看著穿著高跟鞋的媽媽從房間裏出來,往我臥室的方向看了看後就走向浴室,她應該是怕我聽到動靜,卻壓根沒有想到我早就躲在不遠處窺看著她。
然而媽媽沒有直接去浴室,而是進了廁所。我偷摸著跟上去躲在門外聽見她用紙巾擦拭的聲音,一個勁兒的吞著唾液。她一定是在擦著父親射出來的東西!
我一邊幻想著媽媽在裏面的動作,一邊脫下褲子掏出了肉棒,正要開始擼管,卻聽見媽媽的聲音從裏面傳了出來。
「誰?誰在外面?」她的聲音發顫,應該是太緊張了。
我知道是自己剛才的動作太大了,所以驚擾了媽媽,趕緊說道,「媽媽,是我,慕白啊!」
「啊!是……是妳啊?妳怎麽……怎麽還沒睡啊?」媽媽一聽到是我,就更加更緊張了,我都能聽見她慌亂地把紙巾揉成一團扔進馬桶的聲音了。
「我……我被尿憋醒了,所以起來解決一下。」我胡亂地找了個借口,「媽媽妳在方便嗎?」
「啊~是……是的!」大概是沒想到會發生這種尷尬的事情,媽媽一時竟有些語無倫次,「要……要不,妳去屋外?」
我哪裏肯輕易放過這難得的機會,連忙說道,「不不不!我能忍住,媽媽妳先解決吧!我在外面等一會兒就好了,再說了外面又黑又冷了,我最怕黑了!」
「那……那好吧!」媽媽居然還答應了!
就這樣,我站在廁所門外,媽媽躲在廁所裏面,僅有一門之隔。
足足有三分鐘,我都沒有聽見一點兒聲響,整個空間靜悄悄的。
「小白……要不……要不妳先?媽媽……媽媽……」後面的內容太羞人了,媽媽說不出口。
我不客氣的「嗯」的一聲,其實心中早有他想!
「咔!」廁所的門被打開了一條縫,緊接著是更多的,更多的!
我握著硬脹的肉棒,雙眼死死盯著慢慢打開的門縫,直到媽媽完全出現在門後。
「啊!」
看到門外的我的模樣,媽媽直嚇得尖叫!
我趁機向前,一手擋住她要關上的門,一手捂住她的嘴巴。
媽媽驚恐萬狀,雙手用力掰著我的手,雙目除了驚訝更多的是慌亂。
我用力擠進狹窄的廁所,然後反手關上門,隨後將媽媽推坐在馬桶上,捂住她嘴巴的手絲毫不敢放鬆。
「媽媽,我……我想……」我舔著幹幹的嘴唇,喘著粗氣說道,「我想……」
心知即將會發生什麽的媽媽「嗚嗚」地用力搖著頭,眼神透露著哀求,雙手用力地往外推著我的身體。
精蟲上腦的我開始懇求她,「就一次!就這一次!」
「嗚嗚!嗚嗚!」媽媽依舊搖頭,眼裏的淚水已經流了下來,然後就被我的手掌截住。
「一次都不可以嗎?我衹要一次就夠了啊!」
我幾乎崩潰,肉棒已經硬到要爆了,再不發泄,恐怕就要廢了。
「嗚嗚嗚嗚!」媽媽雙手合抱在一起,不停的向我求饒,小腦袋左右搖晃著,笑起來很好看的眼睛流出了更多的淚水。
我無視了她的哀求,抱住她的腰將她拉近,然後鬆開手,在她喊出聲來之前就吻住了她的嘴唇。媽媽並不配合,左右搖晃著腦袋,被我壓在胸前的雙手更加用力的推著我的胸膛,整個身軀都在扭動掙紮,這無疑更加激發了我的獸性!
我一手摟住媽媽,一手直接從旗袍高叉處伸進去胡亂掏摸,沒想到的是她沒有穿內褲!大腿的肌膚溫暖而滑嫩,沾染了父親的精液以及她自身的體液的陰毛貼在陰阜上,我的手指在那裏亂戳了幾下,就找到了生我出來的甬道!手指藉著那些體液順利插入媽媽小屄的時候,媽媽渾身一顫,「嗚嗚」地叫的更響了。
「妳看,妳那裏都濕了!是爸爸的精液還是妳的淫水?妳一定很想要了吧!」我用言語羞辱著媽媽,手指卻沒有停止動作,不停地扣弄著媽媽的屄肉,然後感受著她在我懷裏不停的顫抖,就會獲得莫名的快感!
母子倆就保持著這樣的姿勢,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裏開展了持久的拉鋸戰。
我的手指深入到媽媽的體內,那裏面很暖很滑,待會兒插進去一定很爽!一想到這裏,我就更加賣力的扣弄,直接就伸進去兩根手指,我要把父親的精液都掏幹凈!
「唔?嗚嗚!嗚嗚嗚嗚!」
突然,媽媽整個人都開始劇烈地扭動起來,一雙大腿左右搖晃,最後猛地一夾,發出長長的「嗚」的一聲,本來還在推著我胸膛的手臂就沒了力氣。
她高潮了!
我插入媽媽體內的手指感覺到一股暖流衝了出來,趕緊就把手指抽了出來,緊接著就是「嘩啦啦」的水聲,濺在我腿上的也不知道是尿還是媽媽的淫水。
我抱著渾身癱軟的媽媽,終于沒有再去封住她的嘴巴,因為她已經暈了過去。
我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所以衹能緊緊地抱著她,感受到她高低起伏的胸部,才稍稍安下心來。
然而,忍不住慾望的我還是撩起她的旗袍,一手扶住她的身體,一手握著肉棒慢慢向她靠近。
龜頭已經感覺到陰毛的存在了,衹需要用力一插,就能完完全全的進入到媽媽的體內。可我並沒有這樣做,衹是握著肉棒不停的磨蹭著媽媽的陰唇,單單是這樣的接觸,我就差點忍不住要射了!
這是我的親生媽媽啊!
小說和毛片裏頭的母子亂倫,那都是假的,這可真的是我的媽媽啊!生我養我的親生媽媽啊!
我一想到這,就難免心血澎湃,呼吸急促,握著肉棒的手都止不住顫抖了。
「嗯~」
媽媽終于醒了,慢悠悠的睜開眼睛,吐出了一口濁氣。
「媽媽?」我輕聲叫道,卻在下一秒捂住了她要喊出聲來的嘴巴,「噓!不要激動!萬一驚醒了爸爸,妳我可就慘咯!」
一聽到我提起父親,媽媽的情緒就更加激動了,再次掙紮起來。
我閉上眼睛,感受著龜頭處傳來的快感,笑出了聲。
媽媽這時才察覺到異樣,自己兩腿間有根火熱的東西正頂著自己的私密處,每一次的扭動,陰唇都會擦過那個粗碩的圓圓的頭部,身為人妻的她深知那是什麽,不正正就是眼前這個禽獸兒子的龜頭嗎!看著兒子無比享受的表情,她再次流下了屈辱哦的淚水,身體也不再胡亂扭動。
媽媽一停下來,我就睜開了眼睛,看著她哀求的神情,笑了笑說,「媽媽,舒服嗎?」
媽媽潮紅的臉蛋分不清是汗水還是眼淚,衹是一次又一次的搖著頭,發出「嗚嗚」的哀求聲。
「更舒服的在後面呢!」我邪惡的笑了笑。
用力將媽媽摟緊,我完全不用任何輔助就用龜頭叩開了回家的大門,兩片陰唇被龜頭狠狠地分開,緊接著就是用力的,插入!
「嗯!!!」
媽媽睜大眼睛,死死地盯著我,帶著恨意的眼神極其尖銳冰冷,最終卻還是被性起的我無視掉。
長十二公分的肉棒一插到底,滑嫩的肉壁被強硬撐開,敏感的龜頭撞在了一處更加柔軟的地方,幾乎是同一瞬間,我和媽媽都感覺到有一股電流擊穿了彼此的身體。
「啊!」
我激動得大叫出來,衹感覺三魂七魄都離開了身體,整個人都輕飄飄的,腦海裏一片空白!再低頭看媽媽,哦,她又暈了過去。
就這樣,我開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性愛之行——在這個狹小的廁所裏,我射出了人生中最猛最急也最多的一次!
當我把肉棒從媽媽高潮中的陰道裏抽出來時,那些白花花的濃精混合著媽媽的淫水一個勁兒的往外湧出,地板上積聚了一大灘這樣的混合液……
占有了這樣的尤物,我很快就重振了旗鼓。肉棒再次插入媽媽的小穴裏,我將她抱了起來,離開了廁所,向我的臥室走去。